《恶心》:真实的追求与虚假的叙述
《恶心》是萨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这本小说写于一九三一年,那时萨特二十六岁,历时七年创作完成,一九三八得以发表。这本书起初题为《陈述偶然》,后来改为《忧郁》,最后发表时定名为《恶心》。《恶心》的创作过程,正是萨特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四岁经历精神和身份危机的时期。这时他孤独彷徨,无所适从,整天思考着偶然性的哲学命题,这与他的生活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他很早时就开始思索“我来到世上干什么”。这显然是个哲学问题,而萨特倾向于以文学的形式来揭示和表现。《恶心》即是萨特以文学形式表现他年轻时的哲学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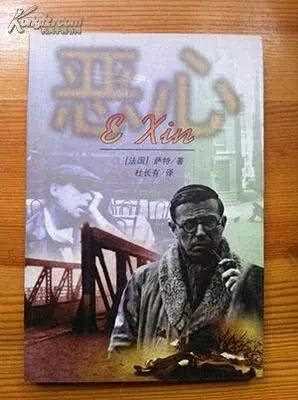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洛根丁的年轻人,萨特没有交代他的出身、来历以及社会关系,把他塑造成一个在异乡的孤独者形象。思考作者的用意,他故意把洛根丁放在一个纯粹的环境里,没有人际关系的牵绊,也没有家庭的负累,更不会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中消沉,他才能与日常生活拉开距离,遭遇到“存在”,思考“存在”的真相。小说没有什么情节,内容确实简单,主人公洛根丁游历多年以后决定在布维尔住下,准备写一位十八世纪冒险家罗尔邦的历史论著。白天去图书馆查询资料写有关罗尔邦的论文,晚上去咖啡馆,有时还和咖啡店老板娘寻欢做爱。一次在咖啡店里,他被一种“恶心”的感觉袭击了,后来他悟出了“恶心”的感觉就是存在的不真实。每当他发现自在存在的事物时,看到事物存在的偶然性时,他总有恶心的感觉。恶心的感觉在这里意味着自我的觉醒,认识到了人存在的偶然性,人的本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这句话原是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说的。也可以说洛根丁也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但他是主动揭开“梦”之面纱的人,并一路寻求可走之路,即使一边寻求,一边破灭,他仍不放弃。洛根丁个人追求存在本质的心路历程,也是现代文明解构的道路。
这篇小说是以日记体的形式写成。萨特选择 “日记”形式其背后有着文化及历史的内涵。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清教徒们将写日记当作是一种自我反省的精神生活,但到19世纪,写日记已经成为平民化、大众化的行为。19世纪是西方中产阶级崛起的世纪,随着社会的迅速转型,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精神折磨:失范、异化、渎神、忧郁、性压抑,孤独,焦虑等,人的主体性意识 日渐崛起,写日记也就成为自我具有独立意志的一种具体表现。正如彼得﹒盖伊在《施尼茨勒的世纪》中写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剖大爆发现象见证了有多少布尔乔亚下了多大决心,要赋予他们的经验和情感一种稀薄的永恒。写日记和读日记都是一种特殊的隐私形式,是体面的布尔乔亚其中一个追求(追求自我理解和丰富自我)的基本构成部分。”日记已经成为中产阶级敞开心扉真诚对待的一个“朋友”,他们把自己的焦虑、孤独、忧郁、压抑写进日记中,以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完善自己,写日记是中产阶级自我认识、自我觉醒的一部分。同样萨特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布尔乔亚,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孤独者形象,他把所有的疑问、彷徨、忧郁以及生理感觉写进日记里,以期以日记记录寻求生存的本质。但同时洛根丁在写日记时对日记有一种质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别将空无吹成神奇,这一点可要注意。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实施窥探,不断歪曲真实。”这也是萨特的质疑,这种质疑来源以文字为生的作家对文字的警惕。萨特写小说时有两种日记的形式,一种是有日期的形式,一种是无日期的形式。记得有人曾说记忆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把时间串连起来,那么也可以说日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这个世界产生秩序感,它使之前、之后以及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有意义。小说开篇是“没有日期的一页”,记录的是没有意义的事。那么对于洛根丁来说,何谓没有意义的事呢,那就是不觉醒的生活,习以为常的状态,他认为像小姑娘那样在一个崭新漂亮的本子上逐日记下自己的感受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自己对生活、人生有清醒的认识,了解并践行生存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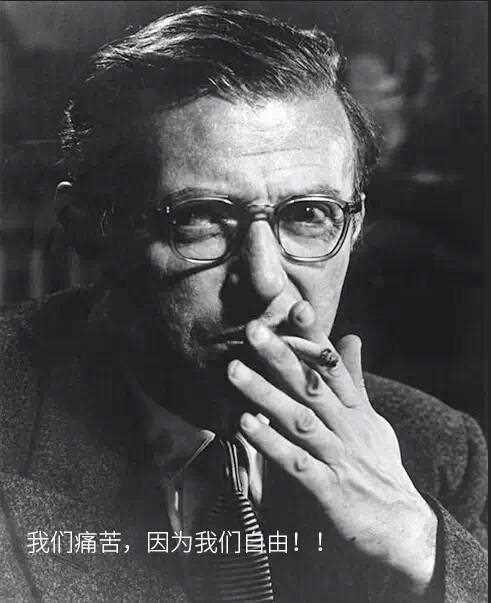
洛根丁一边感受到“恶心”——存在的不真实,一边又寻找真实的存在,却又一次次地发现存在的荒诞。洛根丁来到布维尔暂时居住下来就是想要写一部十八世纪冒险家罗尔邦的历史论著,在一开始他读到有关罗尔邦的传记时被他的生活经历所吸引,后来在布维尔决定研究写作罗尔邦时,他的魅力开始一点点黯淡消散。在大量的资料中他开始有点无法理解罗尔邦一八零一年的行为。历史的书写与这些资料并不吻合,他无法验证历史对罗尔邦的记述和评价是否准确,也无法判断这些资料是否可靠准确,他陷入了一种对历史上罗尔邦的各种行为的怀疑和猜测之中。“是的,他很可能做这一切,但是没有证据,我开始想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证据。这些假定十分恰当,能反映事件,但它们来自于我,它们只是我归纳知识的一种办法。没有任何一点来自罗尔邦。事实是缓慢、怠惰、阴沉的东西,它们顺应我所强加的严格秩序,但始终留在秩序之外。我觉得自己在做一种纯粹臆想性的工作。小说人物肯定更真实可信,而且更为有趣。”洛根丁认为当他自己为罗尔邦写专著时,他所选择的“事实”只是来自于自己的观点,这种认识并不一定符合罗尔邦自身的事实,真正的罗尔邦也许“游离”于“我”的观点之外。最后洛根丁完全放弃了写关于罗尔邦的论文,因为他认识到“侯爵在我身旁,我将自己的生命借给他,直到最后将他安置在历史存在之中。我感觉到他,仿佛他是我腹中的伟人。”,他对罗尔邦的研究是为了逃避自己的无意义的存在,而把历史上的罗尔邦想象成意义的载体,研究他是为了得到一点存在的价值,但结果恰恰是发现了过去的无意义。“这是我的错。我说了恰恰不该说的话。我说往昔不存在。因此,刹那间,德﹒罗尔邦先生就悄无声息地返回到虚无中去了。”洛根丁否定了研究罗尔邦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也是对历史书写的一种质疑,进而也是对将渺小个人与更大的历史意义联结起来以拯救孤独自我的行为的一种怀疑。
以赛亚﹒柏林曾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当浪漫主义革命在欧洲发生时,时代背景是启蒙运动强调以科学代替迷信,理性取代感性,神学上帝从信仰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人们把理性科学放在信仰的位置上。但“启蒙之光虽然给人光明,却不给人温暖,虽然驱走黑暗,却不能照彻人心。”这里更深层的含义是理性并不能给人带来意义感和价值感。这是宗教从信仰的位置出走之后,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显然,人们不满意科学理性这样的一个答案。在启蒙运动之前,也就是在前现代的社会里,人的一生该怎么过,在出生时已经规定好了,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和神学结构决定的,人不需要再去寻找了。但在启蒙运动之后,神学的根基被动摇了,人们再也不能按照上帝或神学规定的意义去划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已不像前近代那样稳定,社会或许有更大的流动空间,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不再是一出生就规定好了,在某种程度上个人有一定的自决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思想和经济的背景下,人需要去确定自己的意义感和价值感的来源。自从神学从信仰的位置下被拉下来之后,浪漫主义者把自我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探索自我,发掘人的内在感性,由内心关照外部世界。浪漫主义者不停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探索,也发现了种种阴面,探索越深,发现孤立的自我也不能成为慰藉心灵的力量,反而使自己变得脆弱。把自我放在信仰的位置之后发现自我无法完全承受信仰之重。“要想从孤独中得救,可以把自己与一个更大的实体联系起来;对很多浪漫主义者来说,民族是具有中心位置的。”绝对自我无法完全给自己意义感和价值感,信仰的位置仍然是空缺的。那么自我认同加上民族认同或许给人意义感、价值感。民族的认同需要借助于语言、历史、神话、民间故事等手段,所以在十八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概念意识逐渐形成。对历史的书写其实来源于一种对意义感的寻求,这种意义感是与一种更为宏大的叙事联系在一起的。而洛根丁对罗尔邦的历史研究也暗合了这一心理需求。而萨特在此对历史研究的否定表达了他对历史叙事的怀疑。而这一怀疑也贯穿在小说的其他叙述之中,他对写日记的怀疑,“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人们会上当的,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它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然而必须做出选择:或是生活或是讲述。”写日记也是一种讲述,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把生活中无条理、逻辑、原由、意义的事件加以编辑整理,使之有逻辑、有意义。这种书写中存在着一种自我欺骗的虚假,与他研究写作侯爵的历史具有相同的属性。也就是说萨特他认为“讲述”是具有虚假性的,无论是讲述他人还是讲述自己。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叙述之虚假性的一个主要部分似乎在于,它假定生活是容易理解的因而是能够控制的。叙述的本质是解释,它会情不自禁地告诉人们事情是怎样的,它们为什么会这样。”萨特在对写日记的反思和放弃对罗尔邦的写作中表达了他对历史、叙述的哲学思考,而这也暗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即将到来。

《恶心》是青年时期萨特哲学思考的成果。洛根丁的疑问、焦虑、思索、追寻也是萨特的,青年的萨特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否定了宗教神学对人的救赎,也否定了个人对国家历史的依附,对社会的权威和秩序也不屑一顾,孤决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寻求存在的本质。但马克思曾说人是政治性的动物,也就是他必须生活于人群之中,萨特把自己隔绝于人群之外,他对存在本质的追求必是艰难的。后来,萨特经历了二战,觉悟人的存在意义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彰显出来,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左派分子,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为自己心目中的美好社会呼吁呐喊,再也没有年轻时的彷徨与无助。他终于找到一条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注明出处:https://www.gouzhua33.com/tuijian/5260420243/17141195912499.html
